requestId:68a103dd7f8a65.01460220.
馮茜著《唐宋之際禮學思惟的轉型》暨喬秀巖序文
-161.jpg!article_800_auto)
書名:《唐宋之際禮學思惟的轉型》
作者: 馮茜
出書社: 生涯·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書年: 2020年9月
【作者簡介】
-118.jpg!article_800_auto)
馮茜,1988 年誕生,四川成共享會議室都人。先后就讀于北京年夜學中文系、歷史系,現為中山年夜學博雅學院博士后,重要從事經學文獻、禮學與禮制史的研討。
【內容簡介】
前人若何懂得“禮”,是禮學思惟史敘述的基礎視角。禮是人爲創作,還是天然天生?圣人制禮的實質是制作經典,還是保留歷史軌制?禮若何實交流現教化的意義?對這些焦點議題的分歧探討,構成了傳統禮學演進發展的張力。
禮學發展到唐宋之際,以文本解釋爲主的漢唐注疏傳統日漸乾涸,宋人開始在“追法三代”的信心下,爲“禮”重建思惟基礎。本書梳理了從趙匡、杜佑、聶崇義、劉敞、陳祥道,再到李覯、王安石、張載、二程、呂年夜臨的禮學研討,最終落腳在朱熹對于分歧禮學方式與思惟的統攝上。這些唐宋之際的思惟家對禮的規范性來源和人道論基礎進行了從頭闡釋,由此實現了禮學思惟與禮儀實踐的歷史轉型。
【目錄】
序文/喬秀巖
緒論
第一節 禮學的類型
第二節 唐宋之際的禮學思惟概觀
序章 后義疏學時代的經典危機
第一節 注疏的文本解釋特征及其式微
第二節 唐代官方禮學的技術化
第三節 玄宗朝禮文之變
第一章 禮義、歷史傳統與中晚唐禮學
第一節 趙匡“禘論”及其經學
第二節 杜佑《通典》與“通禮”傳統
第三節 中晚唐禮書編纂中的禮學
第二章 歷史傳統中的儒學困局:北宋後期禮制變遷中的制禮思惟
第一節 太祖、太宗、真宗後期對晚唐五代禮學與禮制的繼承
第二節 法唐與儒學潛流:真宗朝中后期的祭奠禮制
第三節 仁宗朝禮制中的儒學與“祖宗之法”
第三章 追法三代:禮制復古與考證方式在禮學中的興瑜伽場地交流起
第一節 依經復古:李覯對漢唐注疏的繼承聚會場地與調整
第二節 劉敞的禮經學及其意義
第三節 考見三代:新學與禮學考證方式的發展
第四章 天然之禮與成圣之學
第一節 禮法與成圣:李覯《禮論》及其窘境
第二節 王安石的性格論:基于禮樂論視角的重構
第三節 理學與禮的重塑
終章 北宋禮學遺產與朱子禮學
參考文獻
后記
【序文】
喬秀巖
假如說認識即知差異的話,讀書生怕要分兩種。第一種讀書,即將本身的認知世界與書對照,看兩者之間的差異。第二種讀書,則將其他書與此書對照,觀察其間的差異。第一種讀書,我且叫作“天然”的讀書,是我們平凡默認的讀書方式。我們按本身的興趣看書,沒有興趣的不會往看。拿到書先翻翻,假如內容都是本身熟習的,不會認真看。如有對本身新鮮的內容,了解一下狀況講得對不對、好欠好,好的接收,欠好的跳過。讀古書也這般。我們用本身的常識或“學識”往看古籍,豐富見識,積累組織本身對現代世界的認知,有時覺得書中所述與本身已有的認知有牴觸,則要思慮畢竟是我懂得錯了還是書講錯了。我與書之間,有一種循環交通舞蹈場地的過程,而最后的目標在完美本身的認知世界。第二種讀書,相對于第一種,可以說是「變態」的讀書,我們不是爲進步本身,而是有興趣摸索這部書,才用這種讀書方式。將此書放在其他諸書之間進行比較,我們從圈外人的角度觀察異同,才有能夠比較客觀地評估這部書的特點。不以本身的認知世界爲標準,所以也不難跟別人配合討論研討。
用“天然”的方式讀一部書,每個人的感觸感染會紛歧樣,甚至會產生各種錯覺,有時也構成對此書的錯誤印象。但假如想要進一個步驟清楚書中講的內容畢竟對不對,要做考證,也能得出一個大師公認的結果,會有一種客小樹屋觀性。考證天然需求參照其他文獻,能否也進進了“變態”的領域?我的答覆能否定的,這樣還不夠“變態”,因爲這種考證最后的關心依然離不開本身的認知世界,盡管這一認知世界可以跟“學術界”連通。我說的“變態”讀書,要忘了自我而尋求此書的意義,越過此書內容而摸索作者的思緒。說是忘了自我,讀書的主體依然是我聚會場地本身,主觀性是始終難免的。但這種讀書最后的關心點不在本身的認知世界,而在作者的認知世界,就在這一點上,與“天然”的讀書正相反,所以才叫“變態”。我和葉純芳在“古典與文明”叢書中的兩部《讀書記》想要倡導的就是這種讀書方式,我們認爲學術史、思惟史的研討要自覺消除“天然”的讀書方式,采用“變態”的讀書方式。
舉一部社會學經典爲例,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力》,我看無妨視爲一部思惟史研討的名著,並且其研討方式很有特點,很是值得參考。不少人認爲此書主張新教思惟孕育了資本主義,而這偏偏是韋伯本身在書中明確否認的說法。這種情況正如不少人認爲《菊與刀》提出“罪文明”“恥文明”的對立概念,而本尼迪在書中明確講到這是人類學的常用概念,同出一轍。這些誤解,只需認真看一遍,應該不會產生。但良多人看這些書,都用“天然”的態度,只想了解作者的結論,因此書中的主張被極度簡單化,結果構成違背作者原意的印象。我們略微“變態”一下,關心韋伯的研討伎倆,會爲他凸起的學霸特徵覺得震動。學霸很是周全地彙集相關的以往研討,對共享會議室每一種研討都做過精細的評估,私密空間然后應用這些結果組織本身的研討。論述特別重視邏輯的嚴密,他了解新教思惟與資本主義產生之間的因果關系無論若何都無法論證,所以徹底教學放棄因果關系,限制本身的主張爲兩者之間存在“親和性”。“親和性”只是主觀認定,不需求客觀證據,別人很難說你不對。再說著名的“理念型”,他也有很細心周密的一套解釋。他描寫一個人物,講他的經歷以及思惟和行爲,說這是一個“理念型”,絕不存在完整合適這一故事的真實人物,但這一虛構的人物最能代表一群人的配合特徵。他本身都說這絕不是真實的情況,別人很難批評你。既然周全接收以往的研討,他本身從頭組織的敘述又很充實風趣,並且敘述方式嚴謹守舊,很難抉剔,學界不得不承認是最偉年夜的新結果。可是“親和性”這種結論太過守舊,守舊到幾乎等于什么也沒說,所以眾人不論教學場地作者本身的否認,還是教學認爲韋伯主張了新教思惟孕育了資本主義。
十多年前我偶爾買到一本《鄉土中國》,一口氣看完,嘆服費氏剖析中國社會的深入,而短小的篇幅援用十幾條《論語》詞句來說明中國社會的特徵,印象個人空間尤其深入。這是我“天然”讀書的教學經驗。比來有教學需求,從頭認真看此書,並且對照《菊與刀》、米德And Keep Your Powder Dry(此書似未有漢譯,我看的是日譯本,下文簡稱“米德書”)來看,突然意識到《鄉土中國》即以東方社會學、人類學爲理論基礎。例如在討論法治與禮治、長老統治、血緣與地緣等方方面面問題,剖析“鄉土”社會基礎特徵時,《鄉土中國》都要用“社會變遷的速度”來做解釋。中國的傳統社會“社會變遷速度”很低,所以白叟受尊敬,傳統文明受重視。相反,現代的城市社會,“社會變遷速度”高,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地緣而不是血緣,保證這些關系的是合同與法令,這樣才幹發展經濟。米德書討論america小樹屋n社會特徵時,重點剖析american聚會場地與歐洲尤其英國之間的差異,良多現象都用“社會變遷速度”來做解釋。歐洲社會變化緩慢,所以很重視傳統文明,american社會變化很快,傳統文明被媒體裁減。書中提到的具體事例也有相同之處,如米德講到當嬰兒生病時,英國白叟都了解該怎么護理,是傳統經驗,與american家庭沒有白叟,只要被雜志、廣播的意見擺佈分歧。費氏也講過當其避難居云南鄉下時,小孩哭個不斷,當地老太太教費氏用藍布和咸菜擦小孩牙齒,公然見效。很明顯,費氏將米德書論歐洲與american差異的理論調用到鄉下與城市之間的差異。于是我也有事后諸葛的發現,即費氏講“社會變遷速度”的處所講得都非常輕巧,高超高到有些飄浮。原來是因爲拿來用的理論,中間并沒有本身苦心探索的過程。這樣看的時候,我已經踏進“變態”讀書的世界了。
我們要從《鄉土中國》中扣除社會學、人類學的理論原因,扣除干凈之后,剩下的部門才是費氏本身的東西。只要這樣看的時候,我感覺本身能夠更好地體會到費氏熱情瀰漫的精力盡力,頗爲其年輕朝氣所沾染。讀過《鄉土中國》的人,都會留意到全書反復以“鄉土”與“現代”爲相對概念。其實“鄉土”當與“都會”相對,與“現代”相對的應該是“現代”。在此我們要推想在一九四七、四八年那時候,費氏那些高級知識分子都在拼命思慮中國若何實現現代化。在他們的意識當中,中國落后于歐美,要說歐美是現代的話,我們在沒有趕上歐美之前不克不及算現代了。學過人類學、社會學的費氏天然要思慮,中國之所以落后,在社會、文明方面能考慮有什么樣的緣由?于是反思中國社會、文明的“鄉土”性,費氏一方面共享空間以無限的同情描寫、剖析中國的“鄉土”性,另一方面時不時地表現出中國必須走向法治化、商業化門路的思惟。由于當時蘇聯興起,費氏甚至對計劃經濟的可行性也有所考慮。在這里我們看到一個以社會改造爲己任的年輕學者,無邪、認真,充滿幻想,極具時代特點的精力面孔。
《鄉土中國》寫得淺顯,沒有提到什么洋理論,但別忘了費氏是清華的高材生,留英在人類學年夜師馬林諾夫斯基的指導下寫過英文博士論文瑜伽場地,稍早于《鄉土中國》發表的《生養軌制》中屢次援用馬林諾夫斯基的理論敘述,在《鄉土中國》后記中又明確講到受過米德書的直接啟發,我們怎能不看那些書?看過米德書之后,我對《鄉土中國》的懂得完整紛歧樣。並且這些比較和觀察會有必定的客觀性,所以我后來看到japan(日本)一位長年研討中國社會學的學者寫過一部費孝通1對1教學論(佐佐木衛《費孝通——平易近族自省的社會學》,2003年),介紹《鄉土中國》即以馬林諾夫斯基、米德、本尼迪的影響爲主線索。想要清楚《鄉土中國》這部書的意義以及費氏的思緒,不得不看米德他們的書,事理很明顯。又如japan(日本)也有專門研討《菊與刀》的學者,據說有一批信函可證「菊與刀」這一書名是書稿完成后由書商建議的,作者本尼迪據此才加寫了第一章和第十二章的相關內容,又說《菊與刀》有大批襲用Geoffrey Gorer的論述的部門等等。(福井七子2012年的日文文章,英文題目爲Benedict’s,Gorer’s and Mears’view of Japan and Its people)雖然我并不喜歡這種翻渣滓堆式的“研討”,不克不及否認這些信息對我們清楚本尼迪的思慮過程是不無幫助的。
費氏的情況也讓我聯想到郭明昆。我和葉純芳曾經對郭明昆留下的一系列中國現代家族制研討進行過初步的“變態”讀書,將十來篇論文按撰作時間從頭擺列,調查每一篇參考東方人類學論著的情況。(請參《學術史讀書記》所收《郭明昆》一文)結果發現,沒往過歐美的郭明昆閱讀英文論著,緊跟當時東方最新的人類學理論,徹底消化,運用來剖析中國現代家族制,出色無比,令同時期留學american人類學重鎮伊利諾年夜學的馮漢驥看塵莫及。但郭明昆做完這交流些理論剖析,就掉往對理論的興趣,埋頭扎進中國具體現象的具體剖析當中往,一往不返了。費氏的情況也跟郭明昆類似。費氏學東方人類學、社會學理論,學得最透徹,但他關心的是中國的現實問題,東方理論不過是拿來用的東西,用完就扔了,費氏后來也一向跟著中國的現實走。在此我有一個無法論證而抹不往的感覺是,東方文明能否傾向具體實在的思慮,與東方文明愛用抽象概念思慮分歧,利瑪竇說“中國人不會用辯證法”(《耶穌會的中國傳教》第一書第五章),講的也是這個差異?因爲這般,中國社會由個人與個人之間一對一的人際關系構成,與東方人通過抽象概念組織各會議室出租種社會關系分歧,這豈不是《鄉土中國》所謂“差序格式”、“團體格式”的所以然?傾向具體實在的思慮習慣能否讓我們不難急著要結論,較不不難做“變態”的讀書?
以往的中國現代思惟史研討,往往將“思惟”局限爲哲學及政治思惟。我看過余英時《戴震與章學誠》,覺得無聊到很難受,因爲余氏關注的就是「思惟」,而我對這些提不起興趣。我拿過張壽安《以禮代表瑜伽教室》,看書中對凌廷堪的代表作《禮經釋例》充耳不聞,了解張氏也只關心“思惟”,不關心經學、禮學,竟放下未能卒讀。我還見到過一些人,因爲本身喜歡“內圣外王”“經世致用”那一套思惟,愣說現代學者莫不秉持這種精力,不需求論證。以往學界受平易近國“科學”考據學觀念的影響,科學自以爲是的學術標準,討論現代的經學著作往往都要剖析優缺點,哪些做得不錯,又有哪些缺乏之類,構成經學史論文的套路。以本身的標準評判現代學術,作爲“天然”的讀書態度固屬無妨,但不克不及作爲學術史的研討方式。禮制研討,則多由歷史學家奉行,因此不難著重政治意義的摸索。以往這些學者都在用“天然”的舞蹈場地態度進行研討,所謂“古之學者爲己”,都爲了完美本身的認知世界而做的盡力。我們談論思惟、經學、禮制,不難覺得這些都是客觀問題,其實這些問題只能作爲我們的主觀認識而存在,所以這些研討都要在崇奉配合學術條件的小圈子內,互比識見、境界的高下。我盼望今后的學者“爲人”,一來以前人本身的思慮過程爲研討物件,二來做客觀的討論,大師配合研討。現象世界千變萬化,而人類的認知要靠單純的概念及語言。是以,當以前人的主觀爲討論物件時,我們的討論才不難更客觀。舉例來言,若何懂得“新教倫理”,只能言人人殊;假如討論路德著作中的路德的思緒,則應該較不難達到共識。
馮茜研討中唐至北宋的禮學,從杜佑到朱熹,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認識,令讀者另眼相看,琳瑯滿目。對于本書討論的著作和人物,近些年學界已經積累了不少研討結果。馮茜周全把握這些結果,對每一種研討進行妥當的評估,進行選擇性援用,頗有類似韋伯的小學霸氣勢。其實馮茜都親自閱讀原始資料,樹立本身的觀點,別人的研討只要參考意義。馮茜對相關禮學著作進行純粹經學的比較剖析,也從頭探討此中的“思惟”問題,又研討軌制因革背后的動力,均出自創,非常新鮮。當今學界,研討經學、“思惟”、禮制分別都有一些專家,但未有人能兼通這三方面。其實唐宋人本身豈有近代“文史哲”之分類意識?馮茜對這三方面都下過工夫,進步本身的剖析才能,然后忘失落“文史哲”的學術框架,摸索唐宋那些人物各自分歧的學術條件,追尋他們的思緒。這樣才獲得了今朝最開闊的視野,對這時段的禮學史提出了今朝最恰當的新懂得。提出這么多主要的新懂得,凡是要么浮夸,要么煩躁,像我二十年前的博士論文。但是馮茜敘述得淡定無懼,我看是十多年來馮茜孜孜讀書,始終堅持忠實本身的結果。好樣的,愉快。
2018年12月25日
責任編輯:近復
@font-face{font-1對1教學family:”Times New Roman”;}@font-face{font-family:”宋體”;}@f瑜伽教室ont-face{font-family:”Calibri”;}p.MsoNormal{mso-style-name:註釋;mso-style-parent:””;margin:0pt;margin-bottom:.0001pt;mso-pagination:none;text-個人空間align:justify;text-justify:inter-ideograph;font-family:Calibri;mso-fareast-font-family:宋體;mso-bidi-fon瑜伽教室t-family:’Times New Roman’;font-size:10.5000pt;mso-font-kerning:1.0000pt;}span.msoIns{mso-style-type:export-only;mso-style-name:””;text-decoration:underline;text-underline:single;color:blue;}span.msoDel{mso-style-type:export-only;mso-style-name:””;text-decoration:line-through;color:red;}@page{mso-page-border-surround-header:no;mso-pa瑜伽場地ge-個人空間border-surround-footer:no;}@page Section0{margin-top:72.0000pt;margin-bottom:72.0000pt;margin-left:90.0000pt;margin-right:90.0000pt;size:595.3000pt 841.9000pt;layout-grid:15.6000pt;}div.Section0{page:Section0;}
TC:9spacepos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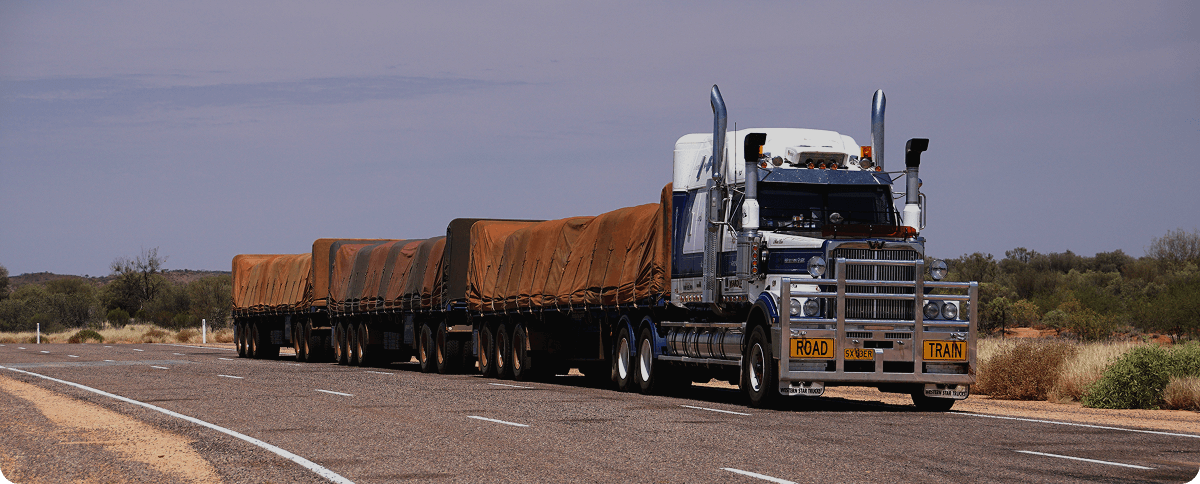
發佈留言